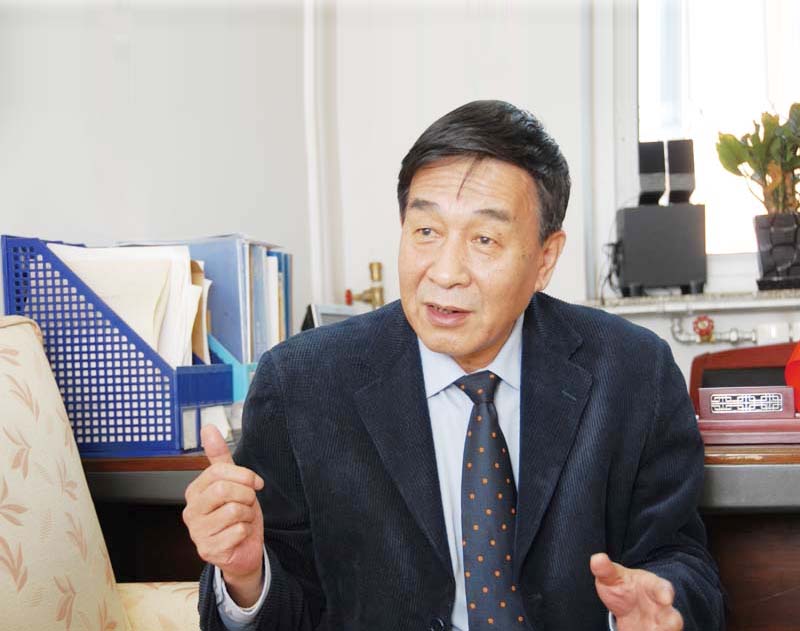乡村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很重要,它代表了稳定、踏实,有叶落归根的意涵,这是乡土社会运转千百年以来形成的一套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其支撑社会稳定。
而土地制度变迁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之间有深刻联络,研究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成因、发展变化及走向,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重要视角。
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是一个有趣的领域。
古今土地制度演变与社会关系变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哪一朝代都有自己的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皇权不下乡”,乡村大部分时期处于宗族治理、自给自足的自然演化过程。
虽然国家权力中心在城市,但资源中心在乡村,因为决定国家实力、军队实力的核心资源是农业生产。
所以,古代社会阶层划分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农民排第二,生活算不上富足,但“名义上”地位并不低。比农高的是“士大夫”阶层,科举制度会推动知识分子进城,其他方面农民没有强烈的城镇户的欲望。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也不是单向性的,士大夫、大商贾功成名就后,会选择落叶归根,回乡买房子置地、建设乡村。城乡间一直处于一个不平等却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这种权力中心和资源中心的长期错位,也造就了“城市吸取乡村资源、维持发展”的格局,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
因此,古代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和投入非常薄弱。
虽然宋代、明代也有一些乡村建设行动,但核心目的是如何更多的获取乡村资源,而不是让乡村发展的更好。
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乡村几千年形成的、自生自灭的历史闭环永远不可能被打破。
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城乡土地价值“剪刀差”两方面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原始资本积累来源。
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资源中心开始向城市转移,权力中心和资源中心都集中到了城市。农村的地位就愈发边缘化,前期的重大贡献和付出被忽视、得不到补偿,将更加走向衰败,这对于社会全局是不利的,对于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接受的。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柴铎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以人为本的、以乡村发展更好为目的的乡村振兴行动,是对千百年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
那么,国家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呢?不同于现代社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土地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

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所谓方里为井,一里见方的一块地,划分为一个井字,中间耕种条件最好的是公田,周围8块地叫私田,分给农民耕种。
农民必须先耕种公田,粮食全部归国家,才能再去耕种私田,私田也要交公粮,剩下的归自己。私田虽然称为“私”,其产权却并非农民私有、不允许交易。
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二权分立”。在和平时期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农民只拥有残缺的土地使用权,生产积极性很低。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对井田制进行了优化。但到了战国时期、天下战乱。私田都无人耕种,公田就更加荒芜了,国家生产力倒退。
秦国商鞅变法设计了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名田制。名就是“功名”。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就能分到一顷宅基地和一顷耕地。
土地私有化极大激励了生产和战斗的积极性,是帮助秦朝统一天下的重要制度。但是,土地全部私有化的最大问题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大量军功地主,也出现了大量失地流民,造成社会动荡。秦朝盛极一时、却迅速衰败。
到了汉朝,王莽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又强行把土地收归国有,分给老百姓耕种,不允许买卖。但是这个改革,既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土地主,也没有争取到老百姓的支持,农民只是从地主的雇农变成了国家的雇农。而王莽的新朝也很快就灭亡了。
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建立了均田制,划出皇家田土,保留地主利益,把无主土地分给私人。建立了一种妥协的混合所有制,兼顾了生产效率和社会稳定,这也成为此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较为完善的模板。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十六字革命方针中,“平均地权”没有实现。城市中还保留租界和大买办的土地,农村中还保留有地主。
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初期,王明等领导人在根据地错误推行“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极端公有化政策。
对比历史,这犯了和王莽同样的错误,既把地主、富农摆在土地对立面,同时也得不到农民的大力支持。土地让农民共同耕种、交公粮,而不是分给农民,这是早期根据地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我党果断调整土地路线,暂时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战,实行减租减息。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西柏坡会议推出《中国土地法大纲》,打土豪、分田地,成为激励士气、战胜敌人的关键。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农民大力发展生产,参军参战,从根本上支援了解放战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建立了短暂的农民土地私有制,二权统一。
但后来,1957年-1978年,随着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推行,农民的土地重新被集中起来,这一阶段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彻底被收回的阶段。

这与其说是学习国际共产主义经验,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土地制度历史的经验。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时期,土地公有化能够使农村较为稳定下来。但连劳动方式都集体化了,比古代土地使用制度更加不利于生产效率提升。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又放开了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对比可见,大包干制度和2000年前的井田制在土地权利配置上,没有本质差别。
可以说,我国土地制度探索仍然没有走出千百年的闭环。
今天以“三权分立”为特色的农村土地改革,是几千年来走出这个闭环的第一步。
土地制度改革启示录
土地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各项制度中重要一环。从古代到现代的土地史演变,我们从历史中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要有选择的平衡土地的“效率”与“公平”。第二,一般需要从公平出发,搭建一个制度框架,然后以公平为目的,在框架中开展相对自由的探索。第三,改革能否持续,取决于是否取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同时也要让“多各方”都能够获益。第四,改革成功,需要灵活运用土地的主导功能和多元化功能。
按照这一指引,乡村振兴中土地利用应该有一个总的路线图:
1.需要让城乡土地间能够实现权力的平视,这是绕不过去的前提。
只有农地能够得到确权保护,农民的财产权意识才能够被激活,才会有市场意识。我们今天的改革征地制度、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正是这样一项先导性的工作。
2.农地改革不是“恩赐”。是农地权能的“恢复”而不是“赋予”。
我们现在对农村所谓“输血”,是因为前期过度“抽血”造成农村“缺血”,只有通过“补血”才能启动农村内生“造血”。农民手里一点资金都没有,就会被资本牵着鼻子走。那么对过去遗留下的欠账,国家的补偿力度也应该大一些。
3.恢复农地本来就应该有的权能。恢复农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的发展机会。

柴铎认为,只有以上三项做好,才能引导各类要素进入农村。而这个过程要可持续,就需要政府、集体、土地利用的各方都能够获得收益。
只要利益分配是公平的,允许各方获益并没有问题。那么,利益分配如何做到公平呢?
“从福利经济学看,应该按照谁出资、谁获益的原则。按照农地达到入市条件、经营获利的过程中,各类主体的投入比例分配;农民的投入,就是土地权益;地方政府调节金也不应超过其投入的实际贡献。”柴铎解释说,这样才能既保障农地利益,又使得农地有人能用、有人敢用,才能建设一个各方地位平等、各自拥有谈判筹码的真正市场。
乡村振兴中,土地功能的应用可能存在六种场景:包括“生产要素、财富杠杆、利益通道、调控抓手、稳定工具、承载空间”。
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并不是把土地都用于经济收益最高的用途。近年来,地方一窝蜂的搞文旅康养项目、特色小镇项目。但是,乡村真正独特资源是非常稀缺的,短期大量项目进入市场必然造成恶性竞争和同质化,导致利润率迅速下降、项目破产。文旅康养在大城市周边也需要分散布局、错位竞争,在中小城市周边发展就存在很大风险。中小城市中,第一代进城人口很多,对于乡村文旅资源的兴趣是很低的,项目自然不可持续。
维持农业主导功能的现状,也可以通过生态补偿、耕地保护补偿、高附加值农产品定制经营和产业链提升,发挥土地利益通道的功能,让农业也能够振兴乡村。我们现在研究“乡村多功能”,根本问题是要从乡村的视角思考土地利用问题,而不是迎合城市。要找准乡村资源和都市需求间的差别化衔接方式。
柴铎指出,为了支持土地多功能的发挥,未来农村土地利用制度需要开展五个层次建构工作:
一是红线框。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生态文明和粮食安全底线思维,明确保护、限制、控制、管理的基本框架。这些红线应该以简驭繁,为探索创新留有余地。
二是模式库。即以务实的态度,在红线框架内,聚焦吸引、促进、培育、经营四方面凝练模式。
三是政策集。即基于服务意识,明确土地利用的责、权、利和各类规范标准。
四是工具箱。包括乡村土地利用项目设计定位、监督跟踪、效益评价、使用调节等等措施和机制。
五是资源流。即乡村发展振兴的人才、用地、资金、科技支持体系。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龙花楼总结道,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空间的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关联土地利用转型和乡村振兴的纽带。急需通过管控土地利用的权属和经营方式等来创新土地管理政策法规及制度,通过理解发生于土地上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将对土地系统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可持续土地利用解决方案,探索土地利用转型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关乎民生、发展、稳定。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和土地利用转型阶段,由此必然带来特定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土地利用管理改革要继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