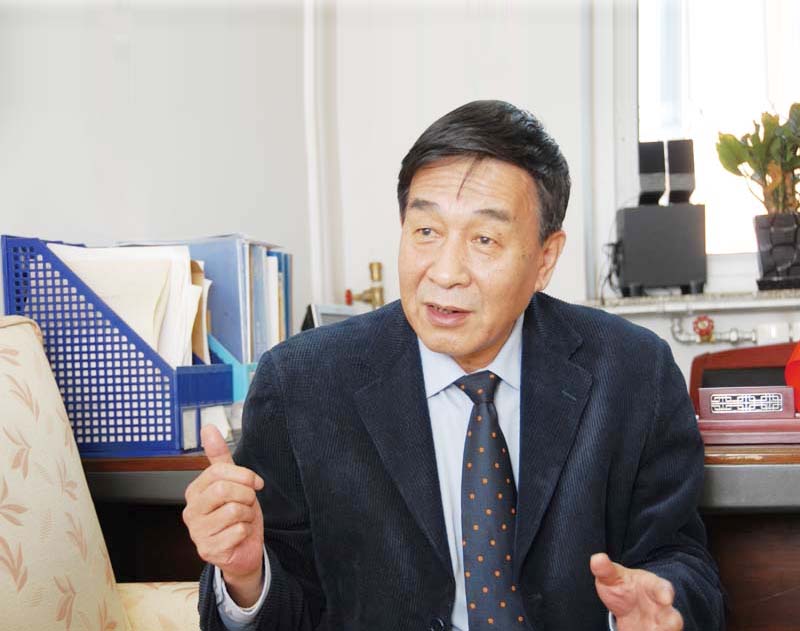[一]
我们注定会成为回不去故乡的一代人吗?在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的这一轮从乡村到城市快速人口迁徙的城镇化过程中,注定要失去基于乡村和乡土的故乡吗?且伴随这种失去的还包括群体性的精神失落和无根感。
梁鸿说,自己每年还是都会回到故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个自己出生、生长的村庄,有母亲的坟冢,有自己居住过的老屋,还有散落于乡村小学、故乡小河边的安静、纯粹、甚至有点孤独的青春。
每当自己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坐在母亲的坟冢前,与母亲“对话”,她都能感觉到作为一个女儿所渴望的来自母亲的安慰。
那个老屋虽然慢慢的开始成为危房,自己童年时代的遗存,开始沾满灰尘,但每次站在那里,记忆就会很自然地浮现,甜蜜或美好,痛苦或忧伤。
尤其是那3年小学老师的经历,更是成为了自己今天进行创作的取之不竭的源流。使得自己面对每天快速变化的世界和生活的时候,依然具有“哀痛”的能力,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和作品,用“忧伤对抗遗忘”。
就在我们对话的那个上午,她用家乡话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很显然,那是在和家乡人通话,她也依然和家乡的人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梁鸿依然属于那个她出生和生长的梁庄。
但是,就像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回到故乡和那个村庄的次数或许会越来越少。而在自己的《出梁庄记》一书的结尾处,一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虽让人心绪复杂,但也确实是其有感而发。
梁鸿对那个童年故乡的离开已经成为事实,虽然也会回到那里,但这种回到已经无法避免那个地方的失落甚至是消失。
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岁月中,她生活的全部目标,几乎都与离开这村庄有关。就和她后来在《出梁庄记》中所走访的散落于很多城市的梁庄人一样,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几乎所有生长于村庄的人,都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到远方去,到城市里去,那里才有未来,才有人生。
只是,有的人选择了打工,有的人选择了读书,有的人选择了经商。途径和努力的方式和梁鸿不同,但目标一致。而且,这里的人的出走和逃离,都加速了这个村庄的失落,甚至消失。
从自己的村庄出走,到远方去,一度成为包括梁庄在内的很多村庄最具正确性和诱惑力的价值观。多年以后,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这些村庄越来越成为一个空空的存在:老屋面临倒塌,道路被泥泞所阻断,池塘被淤积,伦理关系被遗忘。以至于,在城市的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版面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故乡的沦陷而感叹。
回到故乡。有的人为了追寻自己童年的记忆,有的人为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源流,有的人因为在城市受到的伤害和歧视。但不管怎样,中国似乎正在迎来一个“回到故乡”的时代,尽管无数的人突然发现,那个出生和成长的村庄和故乡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注定会成为回不去故乡的一代人吗?在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的这一轮从乡村到城市快速人口迁徙的城镇化过程中,注定要失去基于乡村和乡土的故乡吗?且伴随这种失去的还包括群体性的精神失落和无根感。
[二]
在决定回到自己的梁庄,回到乡邻中间,去记录自己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的故事时,梁鸿已经博士毕业,并成为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名老师。在家乡很多人看来,在梁庄的生活已经成为这个丫头的过去,包括在梁鸿的内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在老家小学3年的教师经历,也被更多人认为那是梁鸿终于摆脱了的困境,她已经不属于那个梁庄了。
但是,当时的梁鸿的写作却陷入了一种自我怀疑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欀县梁庄。
那同样是属于自己心灵的故乡。在梁鸿师范毕业后,曾经在那里的乡村小学教过三年的书。在那三年中,她每天就是读书、上课,然后在河边和田地里散步,与自然对话,将自己所有的情感、孤独、梦想讲给自然听。在这里,她跟大自然建立了一种非常安静、内向与亲密的关系,这对于她后来的创作是特别重要的,给予她一片取之不尽的空间。
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
梁鸿说,“当一个人成熟时,就会去寻找自己”。
当自己面临创作上的困惑的时候,回到故乡就成为其寻求创作突破的一个首先想到的路径。于是,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她回到相对于自己生活的北京显得尤其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5个月。
每天,她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
最终梁鸿出版了《中国在梁庄》,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并为其带来了很大的个人声誉。也正是在这本书完成出版后,她开始意识到,她去书写梁庄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是在寻找自己到底是谁。并且,在其看来,她的这两本书之所以得到不少的共鸣和关注,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都开始思考自己是谁的问题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故乡开始成为更多人的内心情绪。
但这正是在这个时候,和梁鸿一样,很多人突然发现,那个存在于乡土和乡村的故乡,却回不去了。
于是,另一个命题出现了,如果已经告别乡土走向城市的人,面对的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土无法回归的失去和失落,且这种失去和失落在人类城镇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这种随着乡土和乡村的消失,我们的故乡感又将如何在我们的城市里得以重建和回归呢?
[三]
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构探索在城市空间构建出基于中国自己文明历史的故乡感,则成为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意味着,在既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精神失落,将如何在城市中得以回归。
从台湾出差回来的梁鸿,至少有两个经历印象是深刻的:一个是在一家祭拜大道公的庙里,她和当地人轻松地讨论大道公,谈话者很自然地请求大道公保佑这位来自大陆的游客健康美满;另一个经历是,她发现,在台湾的城市构成中,高楼和低矮的民房是可以共融的,而且,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多么的难以接受,倒是很舒心。
对于前者,让梁鸿开始思考,我们现在的民间小信仰却总是委屈的存在,甚至偷偷摸摸的信奉。
很多之前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敬畏和信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被当作迷信批判。直到有一天,突然以“大背头佛”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于是,传统进一步被污名化,乡土社会和乡土文明进一步被污名化。
而对于后者,在我们更多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中,总是对代表了一种权威的“东方大道”心存迷恋,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有达到所谓“现代”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
所以,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她开始尝试系统梳理,在努力摒弃对乡土社会一元化、单一的否定思维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将生长于、绵延于传统乡土文明中的情感、敬畏、社会关系、家族感等,在城市空间进行新的建构。而不是说,就像自己的走访中看到的那样,尽管很多梁庄人已经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但他们还是以一个个“小梁庄”存在着,从来没有进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从来不属于他们。那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城镇化道路。
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在城市空间构建出基于中国自己文明历史的故乡感,则成为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意味着,在既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精神失落,将如何在城市中得以回归。
梁鸿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自己不断求学,不断发展,但骨子里觉得自己仍是个很孤僻的人,“我的精神一直在观察和徘徊中,其实没有融入城市,即使从社会结构上融合了”。
在其看来,很多人的自我已经淹没在历史与现实的急流里了。但最关键的是,这些都是非正常状态的消失,是由于快速、不合理的发展所致。
因此每个人都有了危机感。那种茫茫的危机感、失落感、惆怅的感觉,让很多人不仅有一种对一个村庄的危机感,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危机感。“于是,很多人开始想找到自己,回到故乡”。
当然,这每个人都想要回到的故乡,可能在乡村,也可能在城市。而且,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让每个人都能回到属于自己的故乡,才是我们追逐的未来,也是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未来。
在城市建构每个人的故乡感
《21世纪》:在您的《出梁庄记》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结论是,虽然很多从梁庄走出来的人在某个城市生活多年,但他们仅仅是将梁庄搬到了这个城市,从来没有真的融入到自己生活多年的这个城市。如果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失败的城市化,甚至连目前媒体上形容的“半城市化”都不算。
梁鸿:是的。你会发现,在这些离开梁庄来到城市的梁庄人的生活中,旧有的熟人社会仍然是有效的,不分好坏,有实际作用,比如,遇到困难和危机能够一起面对,被人欺负的时候,一起打架,遇到经济困难,也可以互相帮助。而且,更重要是,在自己的熟人社会中,农民有来自周围的精神支持与安慰,有实际生存的感觉,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感,离开这个熟人社会,在这个城市就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感,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在走访的很多分布于不同城市的梁庄人生活的地方,就像小梁庄,只是原来梁庄的在空间上的挪移,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的亲情结构、亲密关系,一并搬到了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个懒惰的人,在他家乡河南的那个梁庄被看不起,而到了北京的河南村依然被看不起。不管在哪里,他仍然都没有逃脱熟人社会对他的评价,因为,看似已经来到了城市,实际上只是在城市的边缘复制了那个原来的梁庄。这样的人仍然没有进到城里,与北京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这里工作,拿点工钱,并没有建构起自己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活方式,仅仅是用一种不同于农业耕作的方式获得金钱的回报。
《21世纪》: 所以,您的这本书无疑通过一个一个实际的案例告诉我们,之前统计出来的城市化率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是很不真实的。
梁鸿:而且,在统计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已经被统计到城市化率中的人的性格,更看不到他们真实的人生。比如,在乡村中一位50岁的老人,进入城市后做了保安,面对城市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压抑,他的所有品格、情感、温柔、智慧,都只会成为城市里一道模糊的背景。这样的形象太多被模糊化、群体化、符号化了。
《21世纪》: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些从梁庄走出来的人,在城市里继续以梁庄的形式存在着,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必须选择这样的形式。但问题是,城市和乡村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聚居方式,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美好的城市化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传统乡村社会或者乡村空间中所看到的归属感、身份感和温情等,是不是可以在城市空间中重新建构。我们能不能在城市建构起属于每个人的故乡感,通过什么去建构?
梁鸿:故乡感,什么是故乡感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是谁,这可能和你说的故乡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到自己?首先就是要想到父母,在血缘关系中寻找,也就是家族。
我们的家族感,也同样是一种绵延感,可以延续到上几代人,很多代人。比如说,我的孩子的孩子,有一天会来到我现在所居的城市里的老屋,他们也会感受到自己这个城市里存在的一种绵延感和家族感。这种家族感与乡土社会中的家族感,是否有大的区别?也不见得。在南方很多地方,祖上留下祖产,好几代之后的后人还会祭拜他们。
所以说,乡土社会中的结构的确会绵延到城市里去,乡土中国不应该被认为是进入现代社会的阻碍,被人诟病为愚昧的存在,它与城市中国可以融合,非但不会阻碍人的生存生长,反倒可以给人以更好的稳定感,对城市社会的建构是有利的。每个人都需要去寻找根源感与存在的依附感,而这,哪怕是离开了乡土,也是可以重新在城市里被建构的。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一直在用一种一元化的思维、单线的思维去思考,好像要构建现代化、现代中国、实现现代性,就一定要将过去的乡土文明全部扔掉,把那种非常悠远的、非常具有人的基本属性的东西抛掷掉。
在《出梁庄记》中,曾写梁庄一个99岁的老奶奶的去世。这位世纪老人,她活着,是一种象征、一种注视,村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严厉的目光。她死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结束了。传统农耕文明、家族模式和伦理关系在梁庄正式宣告结束。
我们需要一种神性的归属
《21世纪》:这种消失是必然的吗?真的无法重建了吗?最近我在思考的是,是不是可以尝试提炼出乡土社会的“魂”,然后在城市社会中通过一些载体将“魂”呈现出来,也就是在城市里重新建构起我们的故乡感。
梁鸿:其实你说的“魂”,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一个寻找自我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连自己爷爷奶奶的名字、生日都不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过去、自我的内在都不感兴趣,不会去对自己的历史性进行了解,浮躁的、飘的氛围弥漫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背景下,要呼唤这个“魂”,要从基本的常识来找,用最根本的方式找到自己。不仅要从家族来找,从血缘来找,还要从社会关系来找,后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熟人社会。
一个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其职业发生了改变,其社会关系也理应发生改变,在这个社会关系体系中,基于自己的职业,应该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和新的评价,并通过这种身份感在周围的世界中找到自己,这样才有存在感,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但是,我的走访发现,这些从梁庄走出去的人,尽管在自己落脚的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感,也就是说并没有建构起在新的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就没有身份感,最终只能在原来梁庄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感,自己的尊严和精神安慰。
而事实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应该能够通过提供就业,从而为就业的人提供职业身份,并由这种职业身份建构起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比如,我在大学教书,周围的人对我就有一种评价,让我能够感受到与在家乡不一样的身份感,这种评价对我在城市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是有效的,我是能够通过这种评价找到我自己是谁。但对很多农民工来讲,周围的评价对其在城市建构新的社会关系是无效的,所以,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找不到自己是谁。
还有就是,到我们的小信仰中寻找自己。我去台湾的时候,发现那里有许多庙,很多人信佛、信妈祖、拜大道公。但为什么我们都将这定义为封建迷信,认定这是妨害现代性转化的呢?现在我们的民间,用一种委委屈屈的方式去追寻自己的小信仰,这种委屈的小信仰因此也被扭曲了。
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的归属、一种神性的归属。不仅仅在历史性中,通过家族感和血缘来给自己定位,从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从精神归属和神性去寻找自己。不论东方与西方,这都是对归属感的一种寻溯,寻找一个人与大地和自然的关系。如果不能健康、正常地对待这种神性,它就会以一种更大更扭曲的方式呈现在公众眼前,比如最近出现的那个大背头的大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与此同时,这就是夸大了传统中负面的东西,传统被污名化了,当以这样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就会那样地让人绝望。
对于中国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理解,他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被重新打开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现代话语中,成为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被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信仰的扭曲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扭曲。而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中国被误解了,被与城市中国二元对立起来了,被人们诟病为与社会发展进步不相符了。
需要寻找约束权威的敬畏感
《21世纪》:提到信仰,其中也包含了敬畏在里面,对神性、对未知、对大地的敬畏。很多人问我,我不断表述的乡愁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更愿意将其诠释为一种敬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然的敬畏。但很遗憾,现在对自然的不敬畏却成为了主流的发展逻辑。
梁鸿:在乡土社会中,对自然的敬畏是重要的法则之一,面对自然和大地,冬去春来,日出日落,要有一份敬畏之心,不能触犯老天爷,不能触犯自然,不然会有报应。以此,乡土社会才有一种相互平衡的和谐。而今天却离自然越来越远。怎样把这种对自然和大地的敬畏重置到城市里去?这点是特别值得探究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对周围社会的敬畏,对父母、自然、周边社会关系以及通过自然法则文本化呈现出来的法律规则的敬畏。
《21世纪》: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和规划中,从绿化到建筑,完全被一种权力美学所主导,最终使得城市离人、自然、大地越来越远。在西部的一个城市,周边被沙漠包围,本来城市周边生长有自然选择下的沙枣树,但因为政府觉得沙枣树太难看,太影响城市景观,于是全都砍掉,重新绿化。结果,花了很大成本和精力,也没有能够恢复绿化,对生态影响很大。
梁鸿:现在城市的建构给人以一种幻象,就是以为自己是主人,是自然界最高的领导。那么,这种唯我独大的幻象怎么打破?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推进城市的空间,侵蚀其它的领域,当我们在享受现代都市的成果时,我们也会失去什么?有一天我经过玉渊潭公园那里的街道时,看到那里有一片银杏树,特别好看。突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只剩下一种树了,甚至地球上只剩下人的时候,那会怎么样?没有多样性、没有丰富性、没有参差感了,这多么可怕。
我们以景观的方式建构城市,找一种树当做景观树种在人行道两侧,我们将其变得整洁、时尚与单一,却失去了自然的感觉。单一的视野来自于人性中,单一式的建构背后包含着权威,这是凌驾于某种生活之上、某种自然性之上的。而这些自然的、多元的,恰恰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生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参差不齐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自然去除掉了,就是在把生活也去掉了。像在台湾,大高楼和小屋并存,这样就很好,你尊重别人的生活,尊重他们的小传统、小信仰,也尊重了多元。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试图建构多元文化元素的城市,但骨子里还是有对“东方大道”式的迷恋。
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有达到所谓“现代”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
我们需要去寻找约束权威的敬畏感,主动去寻找不可突破的东西,寻找到我们行为的边界,寻找平衡点,两者结合才可能有真正的盛世的到来。
以社会建设的角度建设城市
《21世纪》: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断裂已经发生,我们对乡土文明的否定和破坏,以及对城市社会的非敬畏化的建构,不是将要发生,而是已经发生。
梁鸿:所以我们急切需要在社会结构的断裂带上寻找到一种弥合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存在于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乡土的也罢,城市的也罢,去重新发现和诠释它。血缘上不用担心,家族关系复制到城市里去,完全可以适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关系。比如农民工,他们作为个体,没有能力去一点一点地建构城市中的家族关系,无法通过社会的方式使他们找到身份的归属感、家族的归属感。城市的规划者们怎样才可以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城市的建设?
一个人在北京的河南村住了20年,他仍然不是居民,还是一个租户,城市发展红利、拆迁补偿款、福利一点都没有,他对河南村的人情世故也一点都不知道,那他到哪里去建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其次,职业的身份感去哪里找寻,我指的是受尊重感。但这里面不仅包括了社会的具体组织建构,也包含了一个社会意识的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完成,需要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是容纳式的。
如果社会意识里有一个视所有人为平等、视一切合法职业为正常的意识,那么农民的身份感就没那么差了。比如公交车上的农民工被人躲闪,那是因为城市没有给他们提供衣帽间。
在乡土社会,农民出门见人时都会穿上一套最体面的“喝茶衣服”。但农民在城市工作的时候却没办法换。在现在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这样最基本的换衣服的地方呢?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城市应该提供这样的地方呢?
社会意识源于最细节的东西的建构,很细小的方方面面领域的建构。社会每天都在方方面面塑造着农民工的形象,通过整个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给予他们。当然也有互相塑造的一面,农民和城市相互的塑造非常重要,这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意识。
现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硬件上出现的符号化、非常恶俗的东西,大家慢慢意识到了,但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符号化的东西、非常恶俗的东西,我们却很难意识到。要在城市中建构乡土社会的“魂”,就是涉及社会关系、自我认知的问题,这些恰好存在于生活中无所不在、最为细小、好像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城市市民的意识和影响,最终塑造一个农民工的形象,以及最终的乡土社会落后、愚昧的形象,这听上去好像很虚,其实很实。
不应将乡村符号化
《21世纪》:在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后,经历过一段很明显的郊区城市化阶段,特别是在汽车和轻轨出现以后,更是使得很多人重新回归到田园居住变得可能。尽管这被有些学者形容为“田园资本主义”,但也提醒我们的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和对田园之间不是必然对立的。
梁鸿:真正的乡村是开放性的,不是固定的,不能把所有东西都看成固化的、不可改变的,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性的名词。为此我们要摆脱很多观念上的束缚。农民可以建家庭庄园,同时农民也应该有自我意识,不能把地弄得乱七八糟。然而现在知识界有些观念特别滞后,将乡土中国固化、符号化了。乡村是个多元的乡村,要找到适合自己村庄的模式,而模式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对于有很好的古建、自然资源的村庄,就不能让其消失。在反对单元的思维下,我们要建构各种各样的乡村,建构各种各样的城市。
我们要依据乡村各种各样的山川地貌、历史资源去调研,去思考,来让乡村成为在当代社会具有活力的、多元的、独我的乡村。而不是一味地粗暴地强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容易“对面不相识”,对自己的村庄都不了解,这根源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在地教育”,我们都一直在接受普通知识教育、公共知识教育。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村庄,不知道村子里的历史人物,不知道我们的源流在哪里。而这些都不包含在我们现在所学的课程中。如果只是听老人讲,那是特别不系统的。
比如,我知道梁庄里一条河流的来源,当我走在河边的时候,肯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我不仅有现在,还有历史,河流仿佛就从时空穿越而来。但现在人都缺乏这些,都急于往外面走,不了解身边,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村庄,不了解属于自己的那条河流。
《21世纪》:如果你回到乡村,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的思维都变为,要离开那个乡村,到城市去,只有到城里去,到越远的地方去,才显得一个人有出息。逃离乡村和乡土,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
梁鸿:是的。现在教育基本匮乏的,就是不教孩子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故乡。却告诉他们那些是落后的,古典主义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河流、土壤、和它上面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在我青少年时期,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甚至是有一点自闭的人。我在师范毕业后,乡下住了3年,做乡村小学教师。我们的小学离村庄有500米,后面是庄稼地,前面只有一户人家和很多坟,这应该是我度过的最孤独的三年。因此,我20岁以前的生活,对乡村、对自然的感觉是极其深刻的。我每天除了教书,就是散步,静静地散步,所以我跟大自然建立了一种非常安静、内向与亲密的关系。这对于我后来的创作是特别重要的,给予我一片取之不尽的空间。那种自然的、安静的思考,对一个人精神内部空间的拓展是无可比拟的。
在来到北京求学之后,时间飞快,非常忙碌,但我的思维却时常停留在20岁以前,停留在那段日子里。自然给予人的精神的完整性,那种帮助,那样一种开拓,对每个人来说,其重要性和根本性,是无法用其他任何一种东西可以相比较的。这么多年来,我不断求学,不断发展,但骨子里,我觉得自己仍是个很孤僻的人,这让我能够冷眼旁观,我的精神一直在观察和徘徊中,其实没有融入城市,即使从社会结构上融合了。因此当一个人成熟时,就会去寻找自己。而怎么找。其实在城市和在乡村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心安之处是故乡: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精神失落与回归
很多人的自我已经淹没在历史与现实的急流里了。但最关键的是这些都是非正常状态的消失,是由于快速、不合理的发展所致。因此每个人都有了危机感。那种茫茫的危机感、失落感、惆怅的感觉,让很多人不仅有一种对一个村庄的危机感,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危机感。于是,很多人开始想找到自己,回到故乡。
保留重回故乡的可能
《21世纪》: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为一种回到故乡的情绪所牵绊,却发现已经没有回到故乡的可能了,那个属于自己心灵的故乡,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找不到了。如果一个国家,几代人都陷入故乡沦陷的时代失落之中,这个国家又将走向哪里呢?
梁鸿:这也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建几栋房子,让农民上楼,农民就幸福了吗?土地也没有了,内心的依托也没有了,出去的人发现家也没有了。全新的存在并没有全新的、完整的、有根基的结构来作为依托,过去被连根拔起,新的还未能承接上来。这样一来,一个生存共同体是很难建立的。
一个农民,有一个院子、一口井、几棵树,那是一种物理的生活空间,背后是有一种生活方式,再背后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基础,因为物理空间一定会决定你的精神基础。现在我们把这个物理空间一下子拆掉了,又变成了一种精神错位。而新的空间结构没有基于精神的建构,其中包括有很多最基本的、很复杂的细节。
《21世纪》:那又如何通过物理空间的建构,来实现乡土社会的灵魂在城市空间里得以延续呢?
梁鸿:比如,拆迁之后的农民,要不要祠堂就是一个问题。像福建培田古村落,政府支持、呼吁,去修建旧建筑,旁边还有一个新村,条件很好。那么,新的村庄要不要祠堂?要,或者不要,又分别意味着什么?显然,现在是不要的,那又会缺了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来建构这种家族感和绵延感?因为祠堂是一种有形的方式。这问题真的太重要了,真的需要学者去好好考虑了,然后再给政府施加他们的影响。
《21世纪》:就在来采访您之前,我一度担心自己陷入乡村主义而无视城市化的大势所趋,后来,我希望找到一条在城市空间建构起每个人的故乡感的可能。但后来,我看到有关台湾作家席慕容的访谈,她说自己在看到内蒙古草原时,会感动地落泪,但她当时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她将内蒙草原称之为“原乡”,是其精神和内心最遥远的、最根本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地方重新架构其自己的故乡感,但多年以后,我们的原乡还存在吗?是否又会陷入原乡不在的失落?
梁鸿:原乡是一种永恒的、最根本的意象,是超越具体的故乡的。原乡神话,像沈从文的作品中体现的那样,是附着在精神的安居感的,是一种诗意的栖居,看到原乡的意象时,我们会激动。比如刚才提到的我家后面的河流,还有家乡的苦楝树。当我去台湾时,看到了苦楝树,我马上就想到了家乡的树,开着紫色的、清香的小花。我当即就向主人要了几颗种子。因为这是附着在我童年的记忆,是原乡的神话,它可以激起你心里最基本、永恒的、心灵的皈依,不分时空,只要见到,你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每个人都有一个原乡,一个超越时空、物象的神话。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小区前有一种树,当他在其他地方看到时,他也会立刻联想。当然,这棵树是否有独我性,有独特的感情连结,也很关键。独我的原乡神话,需要多元的建构,但现在很多东西都太集约化、太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