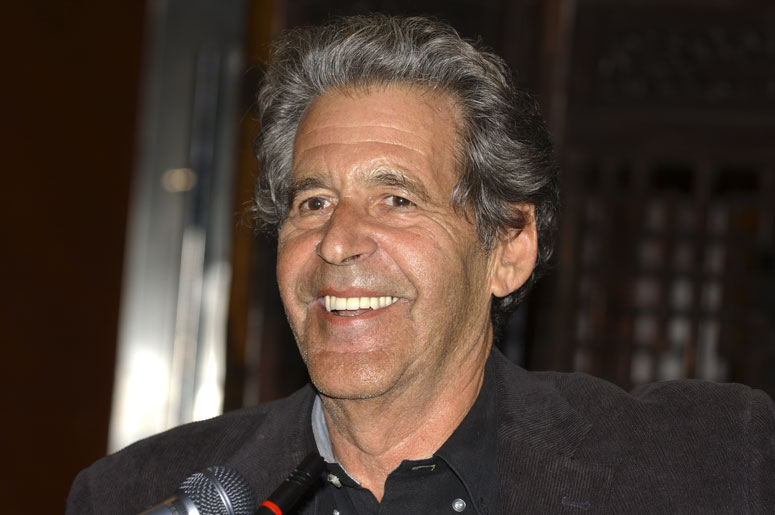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更不是在农村长大。而“农民工”这个称谓,实质上是户籍这堵墙,却如影相随,羁绊着他们融入城市,阻碍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转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
首先,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远离乡土,多数不懂种地,因而对土地没有依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融入”显得异常艰辛。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却与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
半个月前,新任农业部长韩长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里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而只有当他们被赋予“新市民”的身份,他们才会从心理上真正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其次,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高楼鳞次栉比,他们不少能住得起的却只有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城区富丽堂皇,他们的栖身之处却往往是偏远的城郊,甚至简易工棚。据报道,北京全市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而上海市外来人口中也有八成居住在郊区。当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当这些卑微的年轻人经常性地感觉到自己沦为了城市的“边缘人”,当他们的内心被压抑太久的愤懑所支配,谁都不能保证这个群体不会成为城市的一个不稳定因素。2005年末的法国郊区的骚乱或是前车之鉴。
韩长赋部长曾表示,第三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非传统挑战之一”。而这种“挑战”与风险,实际上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部分地化解。
再者,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减少农民工“退保”等社会问题。目前,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个虽然多数时间生活在城里却没有城里“名分”的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多数情况下,农民工能上的医保是农村老家的新农合,而他们长年在城里工作生活,千里之外的新农合即使参加了其实际意义也相当小。不少农民工的社保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就是上了的也存在种种问题。此前南方一些城市出现的农民工“退保”风潮,背后其实与户籍不无关系。如果农民工能解决户口问题,能成为“新市民”,他们何苦背着社保跑来跑去,甚至于“退保”呢?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听到“楼梯响”更要看到“人下楼”,政策基础是有了,指导方针是有了,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政策落到实处,怎么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变为“新市民”。
在全国外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前一阶段已宣布正在酝酿推广“积分制”等办法,打破农民工进城入户“瓶颈”,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无疑就是务实的探索。